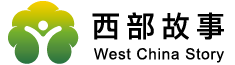生命中的四次生死抗争
年届不惑,回眸四十年的风雨历程,有一种得到上苍宠爱的感恩和窃喜,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死神有四次从我的身边擦肩而过,幸运的是感谢老天的庇护,我都安然无恙地逃过大劫!
第一次
那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学龄前的某年冬天,快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忙忙忙碌碌地准备年货。我家当然也不例外,大人们都忙得不可开交。
这天,二姐与邻居家的姐妹约好上县城买些零碎东西,那时节,自行车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尽管离县城不过十五里的路程,可庄稼人没啥事一年也去不了几趟城,所以进县城逛逛是大多数孩子所向往的奢侈享受。但在寒冬腊月里,人们最忌讳带娃娃们上城,天寒、地冻、路滑、人多、事杂,很容易添麻烦、出乱子、节外生枝。可不懂事的我今天闹着非要跟二姐去不可,看我哭哭啼啼怪可怜的样子,母亲和二姐只好勉强答应了,临行前还给我灌了几片感冒药,生怕路上再受风寒加重了感冒的病情。
一路上的事情到如今我毫无记忆,听大人们说,平时也算听话的我今天跟二姐很不配合,走到哪儿都是吱吱唔唔、哼哼唧唧、别别扭扭。还剩一样东西一买就要回家了,是在旧城南街的商店门前,二姐要我进商店,可不知为啥,我死活不肯进,害得二姐没法,只好嘱咐我在外面原地等着,不要乱跑,她进去买上东西出来便捎我回家。可最让人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等二姐买好东西出来时我却不见了,慌乱中赶紧四处打听寻找,就是不见我的帽盖,直到夜色降临,二姐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回家向父母复命。
要知道,我是家里的独苗,母亲听到这个要她命的消息那还得了,呼天告地、捶胸顿足、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直奔县城的方向,一路上逢人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就那一个娃子……”
好在那年月家家户户都拉了有线广播,父亲在大队任支书,好歹还认识几个公社的干部,几经周折,联系上了公社的“放大站”(专管本公社各村各户有线广播播放的机构),通过有线广播发布了寻人启事。好家伙,这一下可不得了,全公社与我家有关系的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一呼拉全部出马了,但屁大的县城找一个走丢的娃娃还是如同大海捞针,一来认识我的人少,二来根本没有方向可找。
好在我命大,没被冻死,因为老天早就安排好了一个能找得着我的人——我的外爷。外爷在他们村算得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汉:话不多,好苦性,人缘好,尤其在那个赤贫的年代里,能做到“手脚”“干净”(从不拿公家或别人一针一线)更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和称赞。于是生产队便在城南租了一间土屋,特派我的外爷长驻县城,干什么?跟县城各大单位搞好关系,承包他们的的公共厕所,专门为生产队垫大粪,作为生产队肥料的一大来源。凭着他的为人,在这儿已生活了几年,认识的人也不少了。得知外孙丢失的消息,他判断应该在南街,不会走远。于是,捱个打听凡南街他能认识的人,尤其是孩子们。果然不出外爷所料,从一个孩子的口中他得到一个线索:在南街垃圾坑有一个玩耍的陌生男孩跟外爷所描述的身高、穿着和长相十分相似。天啊,那正是我,当人们找到我时,发现我的手里、上下衣兜里全是些城里人用过丢弃的破牙刷和脏牙膏皮之类的垃圾。
后来我能依稀记得的是:父亲和邻居张伯带我到东街的大百货商店给我买点心吃;一路上大人们背着我回家,还时不时听到母亲骂二姐的声音;睡在家里厨房炕上,周围站满了前来探视的父老乡亲;半夜我每次醒来,总看见母亲半坐着望我,说我总是被惊得睡不踏实……其它的事情我是一概不知、毫无印象。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别无他话,只想说:唉,我那可怜的外爷,我那可怜的母亲,我那可怜的二姐!
第二次
我入世总是比别人迟,八七年参加工作,九零年才知道文凭比工作更重要,晃然间,我已步入而立之年的快车道,不能立业,便先成家。
说来可笑,外面找了一大圈,也谈了若干,高不成,低不就,到头来才发现:原来她就在我跟前。九三年六月一日,这个本属于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却成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刚刚度过蜜月,暑期即至,我便匆匆踏上了去省城函授之暑假面授的汽车。凡有函授经历的人便都知道:平时明明偷懒却藉口工作繁忙和杂务琐碎云云而疏于看书,直到面授在即,各科考试接踵而至,才开始像掐了头的苍蝇四处乱撞。好在天随人愿,所考科目侥幸过关,函授部安排休假一天,新婚燕尔的我是喜不自禁,兴冲冲踏上了回家的末班汽车。二个小时的车程,已到家乡的地界,听到车上的客人们在纷纷谈论着最近几天连降大雨,庄浪河水暴涨的事情。因为是在夜里,尽管三一二国道与庄浪河并排逆流而行,毕竟隔着一二公理的距离,加之盛夏茂盛的树木和庄稼的阴翳,透过车窗,河水时隐时现,流量大小的确是不明就里。我的心中开始打起鼓来:从柳树下车,顺利通过龙家湾大桥,可还要徒步绕行二三公理;从牌路下车,打捷道少走弯路,但必须趟水过河……还没等我权衡抉择,缓过神来时车已驶过柳树下车点,分明是潜意识已替我选择好了走捷径。下车,向西,越过公路,摸到通往庄浪河的便道,耳膜已捕捉到洪水的呜咽声,空气中弥漫着本地山洪所特有的腥膻味。我的头皮开始发麻,但还是强打着精神。循着狗叫的声音望去,河东岸砂石料场工棚内的电灯还亮着,估计会有守场的人,于是我一边提防着将铁绳拽得哧啦乱响的狗,一边深一脚浅一脚的朝灯光方向探路。一定是狗的狂叫引起了主人的注意,忽然,工棚的门开了,出来一位高个子男人,看不清模样,辨不出岁数,我便停了脚步高声问道:“师傅,河里的水大不大?”“大着呢!”“人能不能钻过去?”“这我就说不上,你要钻的话顺着河道斜斜的下。”说完进屋关门了。想想我问的这话,人家回答得也对呀,我过去过不去他哪里知得道?这可怎么办呢?下车都已经三四十分钟了,这个时候再折转身回去走过桥的路,等走到家指不定就到午夜十二点了,不行,开弓哪有回头箭?倔强的性格再一次占据了上风。我硬着头皮向咆哮的河水走去,虽然没有那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气势,倒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来到河边,脱鞋,卷裤腿,下河。一开始,有点凉,一会儿也就感觉不到了。我小心翼翼地顺流而下,真正叫做摸石头过河。水刚刚没过膝盖,淡淡的月光下的波浪反射到眼中有点眩晕,我有意识地抬头将目光投向远方,尽量不去看脚下的水波,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趟过了大半个河流,不禁暗自庆幸。突然,我的左脚一闪,身体失去了重心,向左微倾,打了个趔趄,侥幸没被掀翻。河水一下子浸透了裤子,淹没了裤腰,河底的沙石在脚下迅速的流失,我倒吸一口凉气,知道自己误入了人们采沙挖下的坑道。所幸的是此时此刻的我格外的镇定,十分的清醒,如果我被洪水冲走,不要说有人救,就连报信的人都没有,从此我便不明不白地销声匿迹、杳无音信,只落得白送马匹一张。尽管我是地地道道的旱鸭子,但趟水过河的基本常识还是有一点的,这个时候绝不可以抬高腿、跨大步,否则水的浮力会让你飘摇不定的。于是我轻轻挪动脚步,慢慢往前滑行,眼看快到河对岸了,不料河岸已被冲刷成了峭壁,凭我“二级残废”的个头在没有攀援物的情况下岸上的青草真正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先将手中的两只鞋子抛上岸,然后踮起脚用两手抓凡是能够得着的乱草。草毕竟是草,哪里能提得起这只慌慌逃命的惊弓之鸟,这条急急逃窜的漏网之鱼?不是被揪断,就是从土质疏松的湿地连根拔起。一次,二次,三次……这可不行,随着脚下沙石的走动,手能触及的范围也在不断缩小,这样下去,就连最后这点“救命稻草”也会被拔光的。我重新调整措施,调理心态,屏息凝神,左脚猛力蹬地,右腿顺势抬起,膝盖用力抵岸,双手紧紧攥住泥土和草皮;提左腿,换膝盖,身体前移,腾手换泥土;抬右脚,蹬岸沿,匍匐……啊,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是如此的踏实!
短暂的歇息,拧了拧裤子上的水,穿上鞋子,借着月光,踩着田埂的草地,大步流星地向家的方向奔去。微风过处,齐腰的麦浪翻滚,一阵阵恐惧再次袭上心头。如果说我胆小怕事、疑神疑鬼,这你就错了,你有所不知,最近传言四起:有辆运狼的货车出事,二三十只狼不慎逃逸,纷纷流浪在本地田野,这广阔寂寥的麦地不正是它们安身立命的好去处吗?我独自一人,无疑于孤身投群狼,让它们分羹还不够塞牙缝,这不正应了“才离龙口,又落狼窝”那句话吗?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是愈想愈怕,愈怕愈急,愈急愈加快脚步,由走到跑,由小跑到狂奔,这二三千米的路程我几乎是一口气跑到家的。当满脸汗水、混身泥水、神色慌张、狼狈不堪的我出现在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电视节目氛围中的家人面前时,着实令他们诧异,我怕为我担心,只用“不小心摔了一跤”的话轻描淡写地掩饰而过。
古话说得好:“隔河不算近,隔山不算远。”“捷路一个月,湾路三十天。”“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生活中无谓的冒险和牺牲都是不可取的,不然的话,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195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