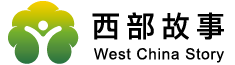今年十二月廿三日是 兄七七忌辰,特為文懷念!
照一般規矩,哀悼故友,應該用「悼念」,但總覺得,若用悼念一詞,還是多少要老道回話,這對一向沈默寡言的老道來說,會是很大的心理負擔;用「懷念」則是我個人的靈性活動,不帶給老道任何壓力。
第一次車禍
今年十一月五日,老道之一的 兄在神州石家莊附近,因車禍身亡,在《 周刋》上讀到這個噩耗,心中的第一個思想,竟然是使自己回想起來都嚇一跳的「殘忍」:「老道終究還是死於車禍!」
原來,像是卅七年前在瑞士曾發生嚴重車禍,車子全毀,車中兩位「老道」( 和鐵口老道),以及後座的辛達謨、吳東媛、劉雲姍皆大難不死,甚至還毫髮無傷(除了劉雲姍被擠斷一根鎖骨之外)。
那是一次由辛達謨帶領,在瑞士蘇黎世一個堂區舉辦的「中國日」;展覽和義賣一些中國式的壁氈聖像、宮燈、扇子等,為臺灣留學生幕集獎助學金的活動。活動結束已是下午五時左右,在準備開車回慕尼黑時,第一件事是「誰開車」的問題;五個人中唯有「筆者」昨夜睡足四小時,其餘四人皆睡眠不足;於是決定由筆者駕駛。「老道」( )自告奮勇:「我坐前座,醒著陪你!讓他們三個坐後座睡覺!」
在大家同念一遍聖母經後,開始上路,很快就進入北上的高速公路;我穩健地握著方向盤,排到四檔,右腳把油門壓到底,一方面聽見後座辛達謨的打軒聲,另方面可也瞄一瞄速度錶:「80」,一直都是「80」!我對老道說:「看!這老爺車今晚也許無法載我們回到慕尼黑了!」已記不起一向沈默寡言的老道說了些什麼;車子開到一處拐彎的路段,就撞到分隔島翻覆了!
車子翻覆後,車頂著地,四輪朝天,順時鐘方向向前旋轉,「駕駛」第一個反應是:伸手找鑰匙息火,怕車子燒起來;一時間就是摸不著。等車子停了,看見前面光亮處,於是爬著鑽了出去;剛站好,看見老道也鑽了出來。理性反應是:車禍中,前座乘客定必受傷最重!今見老道沒事,可斷定後座三人也會無恙;心思尚未定,聽見辛達謨大喊:「快放我們出去!」老道和我還有後面來車的幾個壯漢,合力抬起殘破不堪的車子,救出了另外三位同伴。壯漢中一位義大利人,看著車禍始末,又見五人未死,大叫「Mamma mia!」
氣還在後頭:一輛民間救護車「撒馬利亞」剛好路過,馬上過來幫忙;交通警察也快速呼嘯趕到;救護車要把他們四位送往醫院,而我則要留下給交警作筆錄;老道卻要求陪伴我作證人。終於,證明並非駕車人開快車,而是速度錶失靈所導致,刑責減至最輕,罰款一五○瑞士法朗,作為清除道路費用。(後來保險公司理賠一部同牌同級汽車之外,還讓車內五人免費乘飛機,從蘇黎世回慕尼黑,理由是我們再乘車會有心理壓力;不但如此,他們四位因「交通事故受驚」,每人獲賠三○○瑞士法朗。我因為手握方向盤,腳踏油門,出事受驚,活該!不予理賠,想來雖不合情,卻也合理合法!)
交警記錄了車禍始末:車子過速,彎道上撞上護攔翻覆,車頂著地順時鐘方向旋轉滑行一八五公尺,由此估算,車速應在一三五時里之上,但因速度錶失靈,車禍不全在駕駛人疏失;車內連駕駛五人,未有傷亡;車子則全毀。
其後五人全被送往醫院觀察,三位大男生怎麼也睡不著,於是溜了出去看煙火,適逢瑞士國慶前夜故;凌晨回到醫院病房,護士小姐劈頭就問,昨夜到那裡去了;衹好據實相告,相當無辜地受了一番訓斥。
那次車禍,除了感謝天主大慈大悲之外,(慈悲大概因為車內滿堆了壁氈聖母像,車子翻覆後,聖像包住了車內乘客);除了自我安慰「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之外,老道的「我坐前座,醒著陪你!」以及在瑞士交警前「陪伴作證人」的「友情」和「恩情」,銘刻於心,永世不忘!「老道!真要謝謝你!」希望你在天堂也還可以接受人間世的謝意。
三位老道
從「聖母會」改名換姓成「基督生活團」,再派生出「基督服務團」,前前後後有過三位「老道」,其中二位乃名符其實的「周弘道」和「 」,另一位就是被「封」的「鐵口老道」的筆者。
聖母會改名換姓後,會員連同臺灣聖母會始祖朱勵德神父,通通被丟進了拉圾箱;朱神父和第一代的會員們,也樂意自稱「拉圾箱聖母會」;待朱神父離世升天後,部分會員參加了生活團或服務團,大部分自我放逐,做一個「陽春」教友。
三位老道也分為二派:周弘道和鐵口老道走學術教育路線, 走社會服務路線;若從「存異求同」的觀點去看,二者都在為「福傳」盡心盡力,而且都是「立足寶島」以及「展望神州」。三位老道都同樣兩岸來回奔波,走學術教育路線的,在神州多所重點大學、各大修院講學;走社會服務路線的,在神州各地發展福利機構。
目前,二位名符其實的老道,已離世升天,祗留下名不符實的「鐵口老道」尚在人間世(也許是為了「記載」一些被遺忘了的東西)。二位故去的老道,可以說是「求仁得仁」(引用朱蒙泉神父在今年十一月十九日聖家堂追思老道彌撒中的分享),「死得其時」「死得其所」:周弘道死在上海佘山修院的講臺上,正在給修士們宣講神學; 死在社會服務的路途中;神州原就是「生」他們二位的母親,如今也在母懷中蒙主恩召。
剩下的「拉圾箱聖母會會員」鐵口老道,每年都會至少兩個星期,站在前輩周弘道神父離世升天的講臺上,給修士們講哲學,課前的「天主經」,課後的「聖母經」,都使「尚在人間」的老道,百感交集。
慕尼黑相遇
我和老道首次相識,好像是在辛達謨慕尼黑的住處,當時還有一位「小胡」也在座;和老道打個照面之後,記得只顧和辛達謨談論留學生的獎助學金的事;甚至到離開時,連「再見」都沒有交談上。
倒是在慕尼黑大學Steg-mueller 的「數理邏輯」課上,多次比鄰而坐。由於我的數學程度祇有國中(沒有正式念過高中),黑板上的許多符號都看不懂,老道總也不厭其煩地為我解釋,末了也總會加上一句:「不要怕,數學這東西是很容易的!」(天曉得,他是大學數學系畢業的,而且還娶了數學系助教!)
最後我還是退選了這門老道認為「很容易」,而我只能「望洋興嘆」的課,在大學中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另一個比較常見的地方,是宋老闆開的「武漢飯店」;中國同學在一星期內,吃膩了德國飲食之後,總會到「武漢」去打打牙祭,尤其是剛領到獎助學金,更想大吃一頓。不過,祗要老道在店內打工,他招呼著:「坐!坐!」然後就走去廚房,不一會就端出一盤炒飯:「吃!吃!」連叫兩聲,又去忙他的事!如果你有異議,還來不及開口,他會搶著說:「一碗炒飯嘛!」終究不肯收錢。
老道就是如此,又可愛,又可氣!
慕尼黑那時似乎有五家中國飯店,過中國新年時,總會有其中一家,請中國留學生吃年夜飯,同學們都成了座上客,如果老道在,就只會看見他忙進忙出,不知道的人會誤認他是跑堂的;其實,他的穿著也的確不像客人,不太像留學生。
瑞士夏令營
辛達謨在瑞士舉辦過一屆夏令營,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參加,那是一座樓下開中國飯店,樓上開旅館靠湖邊的房子,參加的同學沒有一個不是趕功課、趕論文,搞得頭昏腦漲的,乘著夏令營想好好「瘋」一下。其中四位身體比較好的,竟破了「三天兩夜」打橋牌不睡覺的記錄;後來被「封」為「嗚呼哀哉」四結拜(嗚是鐵口老道鄔昆如,呼是胡僑榮,哀取諧音區紀復,哉取英文饒姓的J,是饒志成)。記憶中,老道也參加了,不過不是「瘋」玩,而多半坐在客廳一角,閉著眼晴深思冥想。當時,連辛達謨在內,恐怕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其實,也並不關心他的想法。
回想起來,夏令營吃得好,玩得痛快,而對老道的印象不深,總覺得他完全不會玩!好像不是來參加夏令營的。
羅馬聖母會大會
聖母會不像聖母軍,聖母軍以團長為首,而聖母會由指導司鐸作主;而全世界的聖母會的指導司鐸,皆為耶穌會會士;那次聖母會在羅馬伯多祿聖殿內舉辦的「聖母會改名大會」,許多落後地區(買不起機票)的分會,祗有指導司鐸而沒有會員參加。倒是臺灣的聖母會像個樣子,除了從臺灣飛來的指導司鐸鄭聖沖之外,有美國來的焦寶進、比利時來的李秀萍、瑞士來的區紀復、西德來的鄔昆如(已記不起老道為何沒參加),真有全球性、國際性、代表性。
已經記不清三天會議中,討論了並表決了多少提案,印象中,會場呈橢圓形,主席臺可有三個面向;會議語文,除了法、英、德之外,就是拉丁語系的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鄭聖沖神父用不著戴耳機,因為上列的語言他都懂;但他所領導的團隊雖人才濟濟,別的國家在每一提案之後,都圍成小圈,七嘴八舌地討論,唯有中華民國的代表們,好似早已胸有成竹,無需交換意見;到表決時,只聽見鄭神父在說:「焦寶進,妳投贊成票!」「焦寶進,妳投反對票!」「焦寶進,妳投棄權票!」 蓋三個牌子都在焦寶進手上,她負責代表國家舉牌!記得投了兩次之後,焦寶進把三個牌子推給鄭神父,說:「神父!你投!我不投!」
會議到了高潮,討論到「聖母會」改名一案,只見西班牙語系的代表們,群情激昂,反對聲絡繹不絕;吵了相當長時間,尚未有停止的跡象;主席宣佈暫停休息。會議再開始時,即舉行投票,結果是「通過」改名。此時,西班牙語系的代表們掀翻桌子,衝向主席臺,看樣子要揍主席;許多代表想打人的、勸架的亂成一團。
衝突平息之後,主席宣佈:各地區自己決定是否「改名」。
後話不提!
數年之後,回臺大教書,有一天,遇見特敬聖母的奧地利籍耶穌會士龔神父,向他敘述了「改名」的大會「裁決」,他連說:「我就說嘛,那麼好的名字,怎麼說改就改!」 後來聽說,龔神父回到新竹,把他指導的兩個「服務團」的名字,又改回「聖母會」。( 週刊)
970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