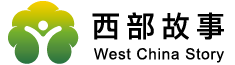康家粉坊
冯平
一连刮了几天的老牛北风,阴沉的天空牛得和保长的脸色一样难看,却又不见下丝毫的雪渣,天气干冷干冷的。康家庄的男人们一大清早就从炕上爬起来,熬上一罐苦茶,胡乱咬上几口馒头,披好旧羊皮袄,来到庄头堡子的高房里。堡子有三四亩地大,里面空荡荡的,只有秋收时留下的麦茬还直挺挺地竖在地里。土地承包到户时,堡子里的荒地被当成三等地分给了懒来顺,来顺不愿要,却又拗不过村长,只得自己种了。来顺懒得出名,地种得丢三落四的,堡子里的麦地到现在还没有耕过一遍。
来顺取出一幅牌,几个人脱了鞋,盘起腿坐在炕上打牌,来顺把炕点得直烙人的屁股蛋。旁边围着一群男人看,喋喋不休地评论着那张牌出得好,那张牌出得臭。输红了眼睛的来顺把牌往炕上一撂,转过头来狠狠地盯住那个说自己臭的男人,说:“有本事你来玩,你来呀!”那男人憨笑着,讪讪地退到圈子外头去了。“娘们儿放个屁,都说香,还说三道四地知道什么是臭。”人群中又传来来顺忿忿不平的骂声和一阵哄笑。
女人们则守在自家的炕头上,一面看着满炕脏兮兮的孩子,一面手里纳着鞋底,心里盘算着过年时给孩子们扯几身什么样的衣服,做些什么像样点的吃喝,体体面面地过个年,免得让来拜年的亲戚邻人笑话。
一到晚上,在外面打了一天牌或者看别人打了一天牌的男人们才纷纷回家,狼吞虎咽地吃下几碗温在锅里的剩饭,就急不可耐地爬上老婆的肚皮,哼哼唧唧地一阵乱动。刚下来时,老婆正待要问个输赢,耳边已响起一起一伏的呼噜,如刚进站的火车。康家庄的冬天从来都是这样。
天总算是晴了,太阳出来了,尽管还是冷冷清清的,可到底有了一丝暖意,至少铺在地上的那片金灿灿的光亮,在视觉上是如此。康家庄的男人们便都跟憋急了尿似的,夹紧旧棉袄,跑到堡子滩里,懒洋洋地靠着向阳的堡墙蹲下,用孩子写过的作业本撕成的纸条,卷起粗粗的旱烟棒子,点燃叨在嘴里,漫不经心地开着粗俗的玩笑,烟卷上的大红对号和错号,随着烟头的一明一灭,一颤一颤地。
这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进了康家庄,像新媳妇撑得圆鼓鼓的屁股一样,吸引了所有男人们惊奇的目光。在人们热烈的注视中,小车缓缓地开了过来,停在了堡子滩前。车上下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黑风衣,皮鞋亮得跟镜子一样,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那人走到堡子门口,看见原来的朱红松木大门不见了,堡子里不知成了谁家的麦地,长短不一的麦茬如倔强的乱发一般竖立着,散发着一股破败荒凉的气息。
那人转过身子,来到人群跟前,给每人发一根纸烟,向其中一位年长的问道:
“大哥,堡子里的康家粉坊再没有做粉么?”
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康家粉坊”这个几乎已被所有康家庄的人彻底遗忘的名词,居然从一个外地人的口中说出。
“你也知道康家粉坊?”被问的那人嘴张得能吞下一个茶叶蛋。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早被拆喽,我都在堡子里种了近二十年的庄稼了。”来顺站了起来,像只公狗那样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打着哈欠说道。
“当年的粉坊把式可能早死得没影了。”有人插嘴说。
中年男子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面部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几下。他勉强地向众人微笑了一下,然后发动起车,走了。那笑容就像是飘在清水煮面上头的几星油花,飘飘荡荡,亦真亦幻。
大家也都起身了,和一群乌鸦一样,双手上下拍打着屁股上和黑棉袄上的土,散伙回家吃饭去了。
来顺也回到堡子的高房里,老婆已经擀好面,就等着他来下锅了。一会儿,跑出去看小车的儿子,流着长长的鼻涕回来了,拉起来顺的手,认真地说:“大,我家的堡子以前真的是康家粉坊么?”
“是的。”
“哪为什么我叫王狗蛋呢?”
“狗蛋,你听我慢慢讲给你听。”来顺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纸,一撮旱烟叶,卷起了烟卷,靠在炕角里,开始讲关于康家粉坊的故事。
康家庄其实最早是一片荒山野岭,漫山遍野都是葱葱郁郁的树林和野草,现在庄里的几十户人,都是祖上从外地迁过来的。那里没有庄名,也不叫康家庄,因为根本没有姓康的人家。
大约是在宣统年间吧,我也记不清楚了,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来顺用火柴点燃烟卷,嘴里喷出一阵呛人的云雾。宣统年间,庄里搬来了一户姓康的人家。几辆马车拉着一对夫妇和一些家当来到了这里,他们雇人盖了几间瓦房,在山坡上开垦了几亩荒地,过着平平静静的日子。那对夫妇不大爱出门,村里人惟一能看见他们的时候,也就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那男人的手又白又细,和绣花姑娘一样,地也种得漫不经心的,不像是在务农,倒像是在栽花养草,消遣一般。
那男人爱喝酒,每过几天,就提着一个葫芦到镇上去打酒。次数多了,就和店主混熟了。店主有时一高兴,叫老婆炒几样小菜,两人一起喝几樽。有一天,酒至半酣,店主说自家的对联年年是请镇上的韩秀才来写的,那韩秀才年愈五旬,虽说只中了秀才,却是镇上远近闻名的读书人,书画琴棋,无所不通,而最令他感到自负的是一手好字。他儿子就在韩秀才的“青梅书屋”读四书五经。今年韩秀才回河南省亲去了,眼看快过年了,自己的手又捉不得笔,不知如何是好。那男人酒已喝得半醉,便大叫:“拿纸笔来!”店主连忙叫老婆取来儿子的笔墨砚台,又取出一张大红纸来,裁成竖条,平铺在桌上。那男人接过笔,蘸饱墨,凝神定气,忽然挥起笔,如一阵旋风般在纸上卷过,一副对联一气呵成,然后将笔往桌上一掷,脚下不称,差点摔倒,店主急忙扶住,已是烂醉如泥了。店主套上驴车,将那男人送回去。在家里,看见一个女人正抱着半本子发黄的线装书看,想必就是这男人的女人了。
转眼年过完了,店主听说韩秀才回来了,就温了一壶好酒,割了二斤猪头肉,吩咐老婆做成下酒菜,自己亲自去请儿子的先生。韩秀才跟着店主来到门口,看见了那副对联,摇了摇头,微微一笑,似乎不屑一顾。又后退几步,仔细端详了一阵,捋着胡须点了点头,神色变得肃穆起来。再后退几步,举头一看,他的瞳孔紧缩,汗流浃背,跺着脚连说几声:“鬼神之笔!鬼神之笔啊!”也不顾店主一家,径自飞奔而去。
后来听人们风言风语的说,康家那男人是光绪爷时的举人,放过道台,不知后来怎么搬到这穷山僻壤的地方。
康家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夫妇俩一心想让儿子好好读书写字,将来有所作为。那孩子倒也聪明伶俐,可惜不爱诗词歌赋,只好舞拳弄棒。长大了,也不务农,集结了庄里一伙年龄相仿的少年,整日东游西逛,争强斗狠,一出门就是十天八夜的,没个定数。老两口又气又愁,相继辞世而去。
一天,少年骑着马回来了,马上还载着一只大箱子和一个年轻的女人。
从那以后,少年再也不闲游闲逛了。他按照女人的吩咐,挖了几个又大又深的地窖,搭起了好几间大草棚,买来了十几个大水缸。等秋后,少年把庄里所有闲余的土豆买了下来,贮存在地窖里。又雇了几个伙计,用礤床儿把土豆擦成丝,放进缸里,然后倒满水。等过几天,把土豆丝捞出来,放掉缸里的水,缸底下就沉淀了厚厚的一层麻白相间的粉面。再往缸里倒满水,用木棍把缸底的粉面搅化了,水也变浑也。过上半天,等水变澄清了,将水倒掉,如此反复淘上四五遍,粉面就变得雪一样白了。这时,女人叫人把装着粉面的缸全搬到一间屋子里。那天夜里,等伙计们全回家了,女人领着少年来到了放满粉缸的屋子里,点起油灯,把门顶上,窗子也关得严严实实的,在里面忙活了一夜。第二天,女人叫伙计们把粉面捏成一个一个的圆疙瘩,放在滚烫的水里煮一阵,她自己用笊儿捞出来一个,一看差不多了,就叫全部捞出来,趁热揉碎了,直揉成面团一样的东西。
女人从她带来的大箱子里取出一个木制的器具,安在锅上。等锅里的水烧滚了,把面团放进去,让两个年轻力壮的伙计在上面用力压,一串白净细圆的面条一样的东西就慢慢地落进了开水锅里。一会儿,面条变得和银蛇一样晶莹透明,柔韧光滑。那女人一尝,熟了,就把粉条捞出来,放进凉水里浸泡,浸好后盘在洗好的细木棍上,挂到木棚里晾晒。
到了晚上,女人取了些粉条,切了几斤猪肉炒了,叫伙计们来尝。那粉条刚挨到嘴边,还没有怎么回味,就和小虫子一般滑进了肚里。果然又精又润,美味可口。女人又取出几把粉,给大家一人一把,说今天头一次开锅,按老规矩,大家应该同喜同喜。
从那时起,伙计们都管那女人叫女掌柜的,而康家那少年,当然是掌柜的了。
经过十来天的忙碌,几个大木棚里晾满了白花花的粉条。掌柜的等粉条干了,就用绳子扎成捆,装上马车,拉到城里去卖。城里用的粉条全是从陕西拉过来的,经过一千多里路的辗转贩运,价格已是原价的三倍多了。掌柜的粉条才卖到市价的一半高。掌柜的把马车赶到一家酒家门口,刚开始,店主一听是本地产的粉条,摇了摇头,说本地的粉条肯定用不成,再便宜也不敢要。掌柜的就说,您先拿一捆试着用吧,我下次还来,如果粉条不好的话,我退钱给您。店主半信半疑的拿了一捆,说:“兄弟,我就当是花钱买个见识吧,咱们这儿还真没听说过有做粉条的。”就这样,掌柜的走遍了城里所有的酒楼饭馆,每到一处,都放下了一捆粉条。
过了几天,他又赶着马车把粉条拉到了城里,选了一片空地,停好车,拴好马,自己就坐在车辕上休息,等着人来买。一会儿,一家酒楼的主人领着几个伙计气喘吁吁地跑来,胖乎乎的脸上渗着汗豆子,说:“兄弟,你的这车粉条我全要了。上次留下的那捆,厨子用水泡好后,韧得和皮子一样,拿在手里抖都抖不断,做成菜后,晶莹透明,圆润可口,真是绝了。我那厨子说,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说着就招呼着伙计们把一粉条一捆一捆地搬走了。
掌柜的套好车,正要回家,又有好几个饭馆的主人来找他,问有没有粉条了。他说已经卖完了,不过明天还来。
“兄弟,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等能耐。没有十几年的功夫,真不敢相信能做出这样地道的粉条。”
还不到腊月,家里的粉条已经全卖完了。
有几个伙计,看着掌柜的在一个女人的指点下很轻易地赚了大钱,心里也有点痒痒。就回到家里,照康家做粉条的方法,自己试着做。土豆丝擦好了,用水淘过好几遍,然后把粉面捏成大圆疙瘩,在开水锅里煮一阵,再揉成面团一样的东西。没有下粉的家具,就用擀杖擀成薄薄的一大张,用刀切成丝,下进开水锅。过了一会儿,一看,早烂成一锅粥了,捞都捞不住。也有人做出来的粉条,能捞起来,在凉水里浸好后,放进嘴里,和皮带一样,嚼都嚼不烂。于是大家在替康家做粉时,特别留意地观察,看和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同。让人费解的是,还是一样的土豆丝,一样的清水淘,一样的开水煮,女掌柜的捞出来的粉条柔而不脆,圆润可口,就是不一样。不过有人发现,在粉面淘好的那天晚上,放粉面的那间屋子的门窗紧闭,还用布堵得严严实实的,油灯整整着了一宵。于是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女掌柜的在做什么,但却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不过再也不做自己下粉的美梦了,只是老老实实地给掌柜的干活。
几个月后,几辆看起来装饰得很气派的马车来到了康家。原来是几个客商,在城里的酒楼歇息时,发现这儿的粉条特别好吃,听店主说当地有一家做粉条的,粉条好,又便宜。这些人一听,想到自己从陕西成千里路上贩运粉条到附近的几个州县,路途遥远辛苦艰难的不说,马都全给跑得瘦骨嶙峋的。一路上费用又高,利钱已经相当薄了。而且风吹雨打跋山涉水的,带着银两拉着货物不安全,稍一疏忽,出点闪失,就要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了。如果附近真的有人能做出这样好的粉条,买来贩运到附近的几个州县,那收益高得多了,又不用受长途劳累之苦。于是他们来到康家看个究竟。
女掌柜的笑吟吟地接待了他们。虽然村庄有些偏僻,粉坊也很简陋,但女掌柜的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热情周到,应付自如。在这样偏僻贫瘠的地方,居然还有如此精明沉着的女人,这大大出乎这些客商的预料。
“听少奶奶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我家里的自小在歧山长大。”
“贵姓?”
“姓杨。”
“莫非是歧山‘粉王杨’家?”
女掌柜的正端了茶水进来,就淡淡地说是。
那几个客商大惊,连忙起身向女掌柜的抱拳施礼。“这些年,我们哥儿几个都是靠‘粉王杨’的粉条才混口饭吃,去年,听说杨家起了大火,一夜之间从歧山销声匿迹了。想不到在这儿碰到‘粉王杨’的后人,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客商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二百两银子,让掌柜的把粉坊建大些,产出的粉条由他们贩运到各地,利钱三七分,掌柜的拿大头,他们拿小头。女掌柜的就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掌柜的招来人,在三四亩大的地上用黄土筑起了大堡子,光堡子墙就有三个马车那么宽,五六匹马那么高。在院子里挖了二十个十来丈大小的地窖,用来贮存土豆;建成两排房子,一排用来磨粉、淘粉和下粉,一排作仓库,存放干粉条;搭起几个大木棚,用来晾粉;还建了几排住人的房屋和一个马圈,让来拉货的客商和车马歇息。另外在堡子的一角盖起了一个高房子,一来看守大门,二来夜里给牲口倒草填料的方便。高房的顶上,斜插着一面红色的锦旗,迎风招展,上面飘着几个大黄隶字——“康家粉坊”。
庄里的种田人一看十年九旱的,收成不好,就留下老人孩子务农,使地不至于荒芜,而精壮的男人都来粉坊下粉,女人们也来干些磨粉、淘粉和晾粉的活计。整个村庄几乎都靠着康家粉坊吃饭。而女掌柜的除了和以往一样在夜晚处理粉面外,其他的活都由伙计来干。
渐渐地,康家粉坊有了五六十个伙计,整日来来往往地在堡子里忙着,每天来拉货的车马如流水一般,络绎不绝。康家粉坊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字号也越来越响亮,最后西北十几个州县的人都吃康家粉坊的粉条。外来的客商不知道这个村庄叫什么,就干脆都叫康家庄了。
一晃十年过去了,女掌柜的给康家生了一个闺女,叫梅花,已经四五岁了。掌柜的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真的视为掌上明珠,万般疼爱。
一天清晨,掌柜的起来,看见地上落了一层薄雪,就叫人去把堡子里外的雪打扫干净,再给马填些草料。一会儿,一个伙计神色慌张地跑来说:“掌柜的,堡子门口冻死人了。”
掌柜的赶紧领了众人出门来看,只见大门前蜷着一个少年,十五六岁的样子,衣衫褴褛,面带菜色,已经冻得半死不活的,怀里还紧紧抱着一只扁担。身旁搁着两只大得出奇的水桶,一只装着旧行李,一只装着一床打满补丁的旧被子,里面蜷缩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睡得正香。
掌柜的吩咐伙计把少年和小男孩抱到一间屋子的热炕上,叫厨房里熬来一碗姜汤,给少年趁热灌下。不一会儿,少年的嘴开始缓缓地动了,浑身只打哆嗦。掌柜的说这孩子看来冻得不轻,给蒙上被子,在热炕上暖一阵吧。那少年便低沉沉地睡了,一直睡到浑天黑。
吃晚饭的时候,女掌柜的端来饭菜,掌柜的叫醒了少年。少年睁眼一看,便挣扎着滚下炕,跪在地上就要磕头。掌柜的连忙扶起,说:“饿了吧,吃点饭,暖暖身子。”
少年端起碗,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向门外看了看。
掌柜的说:“孩子,吃吧。你兄弟我早叫人领着和我闺女在一起了,你就不用惦记了。”
少年一连吃了八碗,这才放下碗筷。他告诉掌柜的,自己叫阿成,是河南人,家住黄河岸边。父亲早去了,母子几个相依为命。今年家乡那边黄河泛滥,田都被淹没了,全家就靠挖野菜度日。一天晚上,弟弟阿详饿得哭个不停,母亲就爬进人家的苜蓿地里,偷着去掐苜蓿叶,给人活活打死了。他用木桶一头挑了阿详,一头挑了些破家当,沿路乞讨,逃荒到这这里。
“老爷,您就收留我们吧,我有的是力气,可以帮您干活。”
掌柜的沉吟了半天,说:“我这儿的伙计都是庄里的,从来没雇过外人。”阿成就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掌柜的还在犹豫,这孩子不知根底,收留他会不会带来什么麻烦。
这时女掌柜的发话了,说:“孩子,起来吧,这么大的粉坊,也不多你哥儿俩。看你年轻还小,就在堡子里打个院,晚上住在高房上照看个牲口吧。”
掌柜的也不再说什么,就说:“孩子,你的身体还虚,先躺在炕上,好好的歇息几天吧。”
阿成这才感激涕零地起来,上炕躺下了。
几天后,阿成完全恢复了,脸上变得红润起来。小伙子浓眉大眼的,就是话很少。只知道埋头干活,将堡子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一天,阿成就取来他的那两只大木桶,来到了女掌柜的跟前,说自己打完堡子,闲得慌,他看粉坊里挑水的人手少,就让他去挑水吧。
女掌柜的一看吓了一大跳,光那两只大木桶就三四十斤重,这两大桶水少说也有二百斤重。再看看单薄的阿成,说你能行么?
阿成说他能行。
那给你换一对小木桶吧。
阿成说不用了,小木桶一个来回挑得太少了。说着就挑起缸一般大小的两只木桶走了。
井在离堡子二三里的小河里。不一会儿,阿成健步如飞地回来了,女掌柜的待他走近一看,水都满到了桶沿上了。
阿成的饭量也大得惊人,一顿饭就是七八碗,遇到过节时,女掌柜的宰羊杀鸡地大操大办,阿成一顿能吃一整只小羊羔,连骨头也嚼着咽了下去。喝起蜂蜜来,一下子三大碗。掌柜的见他忠实厚道,也并不在意。
阿成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对其他的一切不闻不问,沉默得如一块石头一样。只是他的烟瘾很重,拿着一只镶了竹杆的石头烟锅,整日抽得吧嗒吧嗒的。
而阿详一直和梅花呆在一起,两人在一起吃喝,一起嬉耍,一起在堡子院里放风筝,捏泥人,形影不离,甚至晚上两个人都拉着小手睡在一个炕上。掌柜的见梅花有了一个玩伴,心里也十分高兴。时光过得飞快,两人不觉竟都已十七八了。阿详这孩子长得白净秀气,聪明乖巧,又识得眼色,嘴甜得和灌了蜜水一样,七叔八姨地,惹得粉坊里人见人爱。阿详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记性出奇地好。每天来粉坊的马车很多,那辆马车是那个地方的,这次拉了多少粉条,和上次隔了几天,都记得一清二楚的。是个做生意的料,掌柜的打心眼里喜欢他。而梅花也出脱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有一回,阿成就对掌柜的说:“老爷,阿详已经十七八了,不能再吃闲饭了,您就让他干点正事吧。”
掌柜的思索了半天,就说:“阿成啊,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没有一点心眼儿。你就这么一个弟弟,我不想让他再和你一样受苦,干脆就让他跟我管理仓库吧,帮我点个数,记个帐也好。”
从那以后,阿详就跟在掌柜的周围,帮着清点仓库,学着记帐。他脑袋灵,哪家客商拉了多少粉条,给了多少钱,赊欠了多少,窖里的土豆有多少,仓库里的粉条还剩多少,掌柜的一问,都明明白白的。有了阿详,掌柜的着实省了不少心。
一家天水的客商订了五千斤粉条,掌柜的本来要亲自去送,可是这几天他总觉得头昏脑胀的,浑身不自在。阿详就说天水路远,老爷您可能受不了,就让我去吧。掌柜的说,这批粉多,闪失不得,他不放心。但最后又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让阿详去了。临行前,掌柜的千叮咛,万嘱咐,说一路上要小心,还提醒几个车把式多操点心,阿详是头一次出门。于是阿详就骑了马,领着车队出发了。
半个月后,阿详顺利地回来了。他还在天水为掌柜的买了一包上好的茶叶,给女掌柜的扯了二丈绸布,说是从路上的盘缠里省出来的,掌柜的连声夸阿详这孩子懂事。阿详从掌柜的屋里出来后,给了梅花一支精美的玉簪,梅花一把拿过去,羞红了脸跑了。
夜里掌柜的跟女人说:“梅花这闺女都十七八了,也该找婆家了。我看阿详这孩子机灵,是块好料,说不定会使我们康家粉坊更加兴隆。”
女人翻了个身,说:“口善不一定是心善啊。依我看还是先等一等,如果阿详这孩子真靠得住,咱再商量也不迟啊。”
之后,掌柜的就多了一个心眼,有意把一些比较棘手的事交给阿详去办,让他长长见识。而阿详也确实机灵,对掌柜的很微妙的暗示是一点就通,总能使出浑身解数,按掌柜的心思把事情办得干净利落,让掌柜的很满意。掌柜的索性把十来个仓库上的钥匙全交给了阿详,让他看管,甚至想过几天,选一个好日子,把婚事给办了,再把做粉的手艺传给阿详。
一天深夜,天很黑,大家都睡下了。忽然一阵狗的狂叫惊醒了所有的人。掌柜的穿上衣衫到堡子上一看,下面一大群胡子骑着马,打着火把,把堡子滩前照得一片通明。掌柜的到底也是年轻时闯荡江湖见多识广的人,就抱拳说:“各位兄弟,平日我康某人不曾得罪大家,还望高抬贵手。如果想借点钱花,我一定如数奉上。”
“我们大哥不要康家粉坊的一文钱,只要堡子里面的梅花女。”马上的一个人大喊道。
“不交出梅花,我们就要放火焚庄了。”
客商和伙计们都吓得浑身发抖,魂不附体,顷刻,堡子里乱成一团。
梅花也出来了,她在慌乱的人群中寻找阿详,而阿详不见了。
“爹,把我交出去吧。”梅花美丽的脸庞上泪流成河。
掌柜的叹了口气,一言不发地从屋里取出了一柄剑,跨上了马,对大家说你们收拾些银两,趁早从后门走吧,我出去和他们做个也断。说完就催马出了堡门。而粉坊的客商也都牵来马,伙计们马急忙收拾了家当,趁乱从后门跑了。
只有女掌柜的和梅花母女没有走,焦急地堡子上面打转,只见一群胡子打着火把,把掌柜的团团围住,掌柜的手中的剑舞得如雪花一般,不一会儿,好几个胡子落下马去。渐渐地,掌柜的体力不支了,被人从马上砍翻了。女掌柜的一声哀号,一头栽倒,便不省人事了,梅花连忙抱住。而胡子来到了堡子门口,忽然,门口闪出一个手提铡刃的黑影,疯了似的朝那个砍翻掌柜的胡子扑去,铡刃一轮,一双马蹄落在了地上,那人从马上滚落下来,黑影赶上前用力一劈,那人霎时成为两段。黑影又向另一个胡子扑去,只见白光一闪,有人应声落马,接着一个西瓜模样的物什飞了出去,重重地落在地上。而那黑影的腿上也明晃晃地插着一把尖刀。胡子被这不顾死活的打法所震惊,他们打了几个呼哨,拔马退了回去。
一会儿,一个人背着掌柜的尸体一瘸一拐地进了堡子,浑身都是刀伤和血迹,手里的铡刃卷得很窄,还不停地滴着血水。梅花定睛一看,是阿成。梅花一把抱住掌柜的,直哭得死去活来。
这时,阿详才战战兢兢地从马槽里爬出来,浑身沾满了柴草。他把女掌柜的安顿到了炕上,又用冷水浸过的毛巾敷在头上。一会儿,女掌柜的醒来了,又抱着丈夫扑天抢地地大哭。这时,梅花不再哭了,也不看站在旁边的阿详一眼,只是紧紧抱住躺在地上的阿成,用袖子一遍一遍地擦着他脸上的血污。天一亮,她就去镇上买来药,敷在阿成的伤口上,又去侍候卧床不起的母亲。
阿详几天来四处奔走,买来了最好棺木,还请来几个道士,咿咿呀呀地给掌柜的很体面地办了丧事。
女掌柜的病情越来越重,一天晚上,梅花、阿成和阿详都守在她身边。她用手指了指阿详,阿详赶紧凑上前去,“夫人,有什么事您就吩咐吧。”女掌柜的挥了挥手,阿详忿忿地出去了。她又看着阿成,阿成正要出去,女掌柜的摇了摇头,阿成就走了过去。女掌柜的挣扎着往起翻,阿成就用手扶着她起来靠在墙上。女掌柜的把嘴凑在阿成的耳边说:“做粉条其实很简单,只是别人不知诀窍而已……。”最后她看了一眼梅花,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用眼直勾勾地看着阿成,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阿成含着泪点了点头。
那个夜晚,女掌柜的就跟着丈夫去了。
几个月后,阿成娶了梅花,成了康家粉坊的新掌柜的。而阿详,在一天出去送粉条的时候,带着讨回的银子,不知去向了。
老掌柜的死,使许多客商都不愿再来康家粉坊了。加上一瘸一拐的阿成沉默寡言,不善经营,康家粉坊的生意是每况愈下,越来越冷清,好多木棚、仓库都闲下了。
没过几年,西北解放了,康家粉坊被收公了。阿成是附近十几个县唯一会做粉条的人,公社书记对他很敬重,让阿成继续住在堡子里,做粉坊的师傅,让粉坊不要停下来。至于粉坊的名字么,就改成康庄粉坊了。阿成就答应了,也不觉着怎么失落,还是和原来一样默默而认真地侍弄着粉面,让其他人下成粉条,之后他就装满烟锅,不停地抽着。粉坊里的人也都很尊重他,叫他阿成师傅。康庄粉坊的大木棚里,又挂满了白花花的粉条,干活的、拉粉的人来来往往,又热闹起来了。许多上面的领导来公社检查时,都要到康家粉坊来参观一下,还亲自看望阿成师傅,鼓励他好好干,为人民多做贡献。临走的时候,队长给每位领导送上一包粉条,说是一点土特产,留个纪念。
阿成在康庄粉坊平安无事地当了十来年的师傅,他都快一十岁了,也没和梅花生个一男半女。
有一天,队长在堡子里召开社员大会,阿详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还是民兵连长,端坐在主席台上。队长让阿详念公社里的通知,上面说康庄粉坊从此不再做粉条了,全村实行大锅饭,所有人家的大小铁锅一律交公,用马车拉到县里的炼铁厂去。队长补充说,从今后,康庄粉坊改为康庄食堂,就用下粉的大锅煮饭,每家准备一个瓦罐,开饭的锣声一响,就按人头分饭。最后,他领来了一个戴着眼镜一身军装的小伙子,说是北京上海来了十几个下乡锻炼的知识青年,这是康家庄知青小组的组长周刚。
会散后,队长就让阿成一家搬到了堡子的高房上住下了,庄里所有的牲口被赶进了粉坊的马圈里,由阿成喂养。
一天,周刚领着一群知青来到粉坊,说阿成是地主阶级的典型,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把阿成绑走了,粘上纸帽子,挂上黑木牌,到处游行。等晚上回来时,阿成躺在炕上,动都动不了,脖子和手臂上被绳子勒了几道深深的血痕。梅花用毛巾给阿成热敷了几遍,阿成就呻吟着睡去了。
从此,每次在堡子里开会时,阿成都戴着高高的纸帽子,挂着重重的黑木牌,低着头站在会场上。主席台上坐着以前粉坊里的伙计,声泪俱下地诉说康家粉坊地主对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与欺压。阿详也上了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从自己如何成为康家粉坊的童工,一直说到自己的裤腰里带上了康家粉坊的十几把钥匙,就擦干眼泪,停住了。
在粉坊的一间大仓库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每天早晨,队长的哨子中吹,全村的人都赶紧穿上衣裤,跑到堡子里排着长队,挨个儿向画像请示,大概说毛主席您老人家好,我今天要把几担牛粪挑到南山的豆地里去,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之后就深深地鞠上一躬。也有的说去种麦子或者耕地。晚上大家从地里回来后,又排着长队在画像前进行汇报,说毛主席老人家,我今天割了八十捆麦子,一会儿都没歇什么的。阿成也是每天先请示,再去打扫马圈,要不挑着那对大木桶,一瘸一拐地往食堂挑水。晚上汇报完后,就低了头站好等着挨批斗。
一天中午,阿成正在马圈里铲马粪,阿详和周刚领着一群民兵和知青来到了堡子,押着阿成从高房上搜出了康家粉坊的旗子,撕成几半,说是要彻底破除封建主义的“遗毒余孽”,用火点着烧了。阿详哟喝着几个拿镢头和铁锹的人,来到了粉坊的仓库前,说要铲除封建地主的旧产业。阿成踉踉跄跄地赶过去,站在了人群和房屋之间,他看着阿详,说:“阿详,难道你忘了,当年我用木桶把你从河南挑到这里,是掌柜的收留了我们,是康家粉坊养活了我们这么多年?”阿成气极败坏地脱下布鞋,朝着阿成劈头盖脸地打下去,最后阿成抱着头蹲在了地上。阿详又从身后民兵的手中夺过步枪,用枪托在阿成的头上狠狠地击了两下。阿成摇摇晃晃地挣扎着站了起来,一股殷红的鲜血,从他的额头流下来,他的眼睛像毒蛇吐出的芯子一样,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味,在阿详的脸上来回狠狠地舔舐了几遍,就倒在了地上。
康家粉坊几乎所有的仓库和住人的房屋都被拆了,只剩下了村里做食堂和批斗会场的那两间。
等晚上阿成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高房的热炕上,盖着那床打满补丁的旧被子,脑袋上被什么东西缠着,他迷迷糊糊地喊了声梅花,没有人应。他就摸索着点亮油灯,梅花的身子,如渔人钓竿上的一尾鱼,正悬溜溜地吊在房梁上。
第二天早晨,队长吹响了哨子,庄里的人都集合到堡子里,照例排着长队进行早请示,人们没有发现瘸阿成和梅花。
“这些地主分子,就是顽心不改。”队长派几个民兵去高房里揪阿成,一会儿,那些人回来说,阿成不见了,梅花也不见了,阿成的大木桶和打满补丁的旧被子全都不见了。
从此没有人知道阿成的下落。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康家庄的人过完了一个热热闹闹忙忙碌碌迷迷糊糊的大年,又开始收拾籽种,准备春播了。
开春时,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包装精美的粉条,上面赫然印着“康家粉条”几个字,厂址是北京市××街××号。
又过了一段日子,在康家粉坊的大堡子里,一群民工动工建起了好几排崭新的校舍。据说出资者是一名在康家庄呆过的北京知青,那人姓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