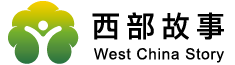“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育一方情。”于是在这座被誉为“鱼米之乡”的汉中市便有了一番别有风味的水土人情。
面皮老汪
汉中面皮起源于秦汉时期,具有悠长的历史。相传汉太祖高皇帝邦在一次微服私访中,路经汉中,偶然食用当地百姓的待客美食。刘邦吃完后龙颜大悦,赞不绝口,信口说道:“此乃蒸饼也。”后来当地百姓改用重叠式竹笼,一次可蒸数张,而且又大又薄。切成细丝,筋丝柔韧,软而不断,恰似皮条,改名“面皮”。至今,面皮已承载了汉中历史数十个祖辈了,成为当地百姓根深蒂固不可取代的独家记忆。
老汪已经蝉联了三届“面皮大赛”的冠军,被大家称作“面皮大王”。在当地人眼中他可谓是:“你可以不知道鹿晗李易峰,但是绝对不能不知道面皮老汪!”老汪在汉中的小吃街租了一间不大的门面经营着面皮店。面皮店的装修陈设有股岁月洗礼过的视感:缺边缺角的桌子板凳,早已被熏黑的白墙以及锈迹斑驳的吊扇。即使这样,每个清晨他的店里都是人拥人挤,生意火爆,引得同行们直恨得牙痒痒。
老汪是位短小精悍的老头,左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的脾气很古怪,还非常的抠门!有一次,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吃完面皮结账时就因为少给了五毛,老汪气的直跺脚,眉毛一横:“你个小娃娃小小年纪就偷奸耍滑,长大了还得了?!你们老师咋教的......”一骂起来就没完,骂得小女孩是坐在地上直哇哇大哭,即便这样他仍然是怒气不消。最后一位老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上来劝他,可老汪不领情,硬是带上老奶奶的一块说教了一番。事情过去没多会,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中年男子来赊账。老汪看了他左边空荡荡的袖筒一眼,微笑着记下了帐,说下次在结。男子干笑着用右手拿起地上装满饮料瓶的大麻袋,一把甩在肩上,慢步向废品站走去。
也不知何时,“老汪面皮店”所在的这条街上出现一条流浪狗,因其毛色偏黄,人们便叫它阿黄,有的人也叫它瘸腿阿黄。
阿黄的右前爪被车轮碾过,骨折了,走起路来也是一瘸一拐的。主人家嫌它没有利用价值了,便绝然抛弃它。它每天都会低三下四的在各个小吃摊前行讨,若是摊主高兴了,就会赏给它一些剩菜剩饭,若如不高兴,便会拳打脚踢,而阿黄每次都会夹着尾巴,呜呜地跑远。
那是一个大年初三的早上,天空中纷纷扬扬地下着小雪。老汪一打开店门就看见缩在屋檐下一隅瑟瑟发抖奄奄一息的阿黄。老汪二话不说便转身从屋里取了条棉毯盖在阿黄的身上,还不惜拿出新鲜肉来喂食阿黄。从此开始,老汪就成了阿黄的主人。
清晨,阳光还未从地平线升起,老汪就挑着灯开始在厨房忙活,阿黄就趴在不远处看着他忙前忙后的身影,有时候老汪也会神经质地和它说说话聊聊天。灯光下的老汪,瘦骨嶙峋,一头的灰白发,脸上的皱纹在腾腾的蒸汽里渐渐模糊。
老汪先在瓷碗里配置底料,调味好油盐咸淡。然后老汪再取下一屉蒸笼,揭开一张热气腾腾的洁白光滑的面皮摊在案板上,刷上一层清油,操练起大刀熟练且快速的将一张白里透黄的面皮切成条状,随后就将切好的面皮用筷子夹进碗里,最后浇上一勺红彤彤的辣油,撒上黄瓜丝或者黄豆芽这样的配菜。就这样,一碗面皮便在他手里诞生了,色香味俱全。这个时候,第一缕阳光也正好洒在碗里,火红的辣子油,洁白的面皮,金灿灿的晨曦,氤氲的蒸汽。它们在这个碗里汇成新的一天和老汪新的期望......
吃一口面皮,咀嚼一下,仿佛点燃沉寂了一个黑夜的心,又往血液注入沸腾因子,人们便会斗志复燃,元气满满,用最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新的一天。如果太过热情也会使人变得暴躁,这时再盛上一碗酸溜溜的菜豆腐来稀释面皮的辣。一碗清淡的菜豆腐像是伴着晨曦而来的风,浸润着你火热的五脏六腑和暴跳的心脏。它们在你的口腔里搅拌,融合,最终流贯全身的每一处毛孔,每一粒细胞,直达灵魂深处。现在,无论是朝气蓬勃的学生还是饱经风霜的工人,他们的眼睛都是亮着的,容光焕发,神清气爽,一切都刚刚好。
忙活了一天的老汪关上店门,一个人坐在刚擦干净的餐桌上,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然后出神地看着照片上那个笑脸灿烂的小男孩,不知不觉间,老汪已泪眼模糊。老汪孤单的身影倒映在阿黄清澈的眸底,显得又苍老几分。
老汪抹去眼角的泪水,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串号码。许久后,电话那头接通了,老汪也笑了:
“小才啊,你没赶上过年,元宵节一定要回来啊。今年我又拿了面皮大赛的第一等奖了呢......”
放蜂人
阳春三月,柳絮漫天飞舞,落英缤纷,恰似寒冬腊月一场雪,但它却没有寒气,带来的是春天的音讯。碧蓝的天空一如水洗,羊儿在天上跑,燕儿在草上飞......站在田坎上,远远望去,漫无边际的油菜花在金色的阳光下尽情绽放。一阵微风袭来,成片的油菜花迎风摇曳,掀起层层涟漪。
油菜花海是汉中一道旖旎的风景线,每年都会招来全国各地数万的游客来观赏,这也成了汉中人的一个经济来源之一。当然,有了花自然就少不了辛勤的采蜜者——蜜蜂。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李哥已经是三年前了,那是我只有七岁,他三十二岁。在我印象中,小李哥是位身材瘦弱,邋里邋遢的无为老青年。他很喜爱作诗,虽然作的并不怎样;他还是一位让我畏惧的放蜂人。
每年油菜花开,小李哥就会带着十几台蜂箱在我家院坝安营扎寨。我有几次向奶奶抱怨说:“奶奶,你为啥又让他来!他会蜇人的!”
奶奶慈祥一笑:“哎呀,你怕啥嘛,过不了多久等油菜花一谢他就走。”
最后我还是被几个雪糕给说服了。
院坝被小李哥和他的蜜蜂军团给霸占了,我每天上下学都会绕很远的路,只为保全我的小命。说真的,我有密集恐惧症,每当我看见那铺天盖地嗡嗡直叫的蜜蜂都会感到一阵眼晕。而小李哥却很喜欢蜜蜂,每天都只戴个网帽,赤着膀子在蜜蜂重重包围中检查蜂箱。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没过几天,我便尝到了甜头——小李哥刚榨出的新鲜蜂蜜。淡黄色粘稠状的液体,还掺杂着几只粉身碎骨的蜜蜂残骸。为了报复我前天被蜜蜂蜇了个大包的仇,我狠狠的吃了一大罐蜂蜜,最后晚上拉肚子,拉了一夜......
小李哥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经常跟我抢棒棒糖,我不给,他就逮只蜜蜂来威胁我,然后我们就打闹在一起,成了忘年交。
熟了才知道小李哥是个文化人,不仅能读书写字,还会针线活呢,比我奶奶缝的都好!至于他会读书写字嘛,那便是他会隔三差五的来强迫我去朗读他写的的诗:
“小蜜蜂,对不起,是我索取了你的性命!你的毒刺刺穿我的皮肤,只不过留下一个小红点,而你却要为此英勇献身......”说实话,我是强忍着吐意的!
“还不如小学生写的呢,你听着,”我揶揄道,“勤劳的蜜蜂,你隐藏在尾部的毒刺是你防身的武器,一生却只有一次机会去伤害别人......”
小李哥听得是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不过我挺欣赏他写的情诗,说是给远在四川的一个姑娘写的,她是他一直暗恋的对象,暗恋了十年。
“她得了癌症,目前还在住院治疗,需要用钱,我想帮她。”说完他含情脉脉的看向院坝里罗列整齐的蜂箱,“蜂箱里的每只蜜蜂只要多采一些蜜,我就能多卖一些蜂蜜,然后就会多卖一些钱。”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总是洋溢着甜蜜蜜的笑容,看着挺傻气的。
所以,这些渺小且充满杀机的蜜蜂却承载着他对她的情。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突发高烧,不巧的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当时我头昏脑涨的,半梦半醒的躺在床上。小李哥碰巧看见我这病殃殃的模样,伸手摸我额头,脸色大变,连忙背上我直奔医院。
风从我耳边两侧“嗖嗖”穿过,其中还携着小李哥呼哧带喘。他的背好硬,嶙峋的骨头硌的我难受。我那时才觉得他好瘦,瘦的只有皮包骨。他一直咬着牙把我送到医院。在医生接过我的那一刹,他“哐当”倒地,不省人事......
小李哥就是这样,从来不放弃,宁愿牺牲自己也得救别人。
他写过这样一句诗:“我仿佛就是一只小蜜蜂,每天都在疯狂的采着蜜,只为给你酿造甘甜的蜂蜜;而我隐藏在身后的利刺,并打算亮出来,因为我会就此丧命而失去采蜜的机会。所以,我从不伤害每一个人。”
来年春天,油菜花海盛开,天地又再次陷入一片金黄。阳光明媚,微风和煦,院坝里空荡荡的,有几只别人家的蜜蜂携着花粉“嗡嗡”地从我眼前飞过。小李哥已经结婚快一年了,以后他不再是放蜂人,是她的采蜜人。
汉山樵歌
被誉为汉中八景之一的汉山樵歌诞生于周朝,距今已逾三千岁了,是陕南民歌的瑰宝。旧时,汉山附近的农民每于农闲时成群结队上山打柴,一面辛勤劳动,一面高声歌唱,此唱彼答,一问一答,故又名“对山歌。”
李老汉是汉山脚下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也唱了一辈子的汉山樵歌。每值农忙时节都会看见他忙活的身影和听见他嘹亮的歌声。
艳阳高悬,李老汉和大家在秧田里忙活。李老汉挽起袖子,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在大家的怂恿下,他鼓起胸腔,扯开嗓子就开唱:
“一担干柴双肩挑,双肩挑起一担柴,砍柴的人儿没柴烧,疾风暴雨天上来......”
歌声高亢有力,旋律明快,却似雷霆乍惊,又好似蛟龙腾海;最后一个尾音拖长像是乌云飘散,终于是雨过天晴。他的每个腔调、字词却都充斥着浓浓的乡土味,很接地气。一曲毕,大家无不精神抖擞了一番又一番!没想到眼前这个小老头的体内居然能迸发出这股惊天动地的气势来,大家无不是暗自称赞他。
或许他是这黄土地的儿子吧,他的魂魄扎根在土里,大地母亲会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力量!正所谓“力从地生”。
李老汉是孤独的,汉山樵歌也叫“对山歌”,可如今也没人能与他对上一番,也只是自娱自乐,自斟自酌罢了。李老汉的两个儿子都有出息,在城里安了家,去年回来想接李老汉夫妇去城里生活,也好尽尽子女的孝道。可李老汉倔的像头驴似的,死活不去,说是城市空气差,也没有人陪他玩,更没有人能听他唱歌。也是,现在的城市耸立着座座高楼大厦,压迫着人的脑神经。街头巷尾也都播着当潮歌曲,都是年轻人的舞台,哪有他这个糟老头子的一席之地?
每当夜深人静,周围都寂静下来的时候。李老汉会独自一个人坐在门槛儿上,抽着闷烟。在夜幕中,忽明忽暗的红色烟头那么醒目,白色缥缈的烟气掺杂着他的愁绪在空气中撕扯,由浓转淡,最后弥散在一阵风里。
社火
热闹的春节刚过,元宵节接踵而至。到了这一天,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吹唢呐,打大鼓。好不热闹!
社火是当地庆祝元宵节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按照当地习俗,元宵节这一天,家家户户老老少少的人都会成群结队的去街上“排街”,看社火。
一大清早,楼上的楼下的,隔壁的对门的,所有人都开始整装待发。老妈照着镜子来回捯饬,就连奶奶也破例穿上大红衣裳;老爸则是一个劲的捋发,小娃娃都把脸洗了个百八十遍!整理完毕,个个都是神采飞扬,英姿飒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全家人你牵着我,我搀着奶奶,一同步行去“排街”。
这大街小巷的两侧的人行道堆满了人。人潮涌动,人山人海,一张张挂着笑脸的面孔彼出此没。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往街的那头张望。
先是一阵喧天的锣鼓声传入耳朵,人海又是一翻腾。父亲把儿子架在肩上,老人们倚老卖老,像电钻似的一下就挤到“浪尖”;人群中不时还会传来一阵妇女的大骂:“是哪个孙子踩我脚了?”“哪个臭流氓摸我屁股了?!”
声音渐行渐近,愈演愈烈。先是一群画着浓妆,脸上都笑开花的大妈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手持两把桃花扇,随着锣鼓声踩着妖娆的步子,一步一摇,放肆的扭动着老腰。紧跟着,一支舞龙队迎来全场的高声吆喝。一条布制的金色大龙张着血盆大口,它在舞龙师的手里活了!柔软的身躯,时而盘旋,时而笔直。好似在腾云驾雾,直冲云霄。随后,人人纷纷仰视,原来是一支高跷队映入眼帘。一群穿着长袖彩袍,浓妆淡抹的“高人”们一前一后,一步一晃,稳步而行。坐在父亲肩头上的小孩们仰视着他们,心说:“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能扯下电线,掀别人家的瓦......”
全镇再次陷入喜气洋洋,人声鼎沸的节日气氛中。锣鼓惊起一片尘土,舞龙驾起一片祥云,目光灼灼的“高人”们展望未来......今年一定会是个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的一年!
夜,从巍峨的汉山的背后拉开序幕,人们这才意犹未尽的散去,喧闹了一天的镇也终于回归了往日的祥和宁静。家家户户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鞭炮声声响,全家人团坐在一起,吃着白白胖胖的元宵,看着窗外绚丽绽放的烟花,年,也算是过完了。
又是一场鹅毛大雪飘飘洒下,覆盖住了旧的一年中所有的美好与不美好,留下的只是充满期许的未来。我们则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下一年。
老汪横抱双臂倚在门框,含情凝睇地目送着那位背着大包小包,在风雪交加中艰难前行的壮小伙。阿黄乖巧的趴在老汪的脚边。壮小伙子的背影渐渐模糊,老汪这才收了神,跺跺脚,拍打去落了一头的雪,抹掉眼角的泪花,擦掉结冰的鼻涕。老汪踟蹰了一会,还是不放心,又跛着脚走了出去,阿黄紧跟着。一人一狗,一瘸一拐的踩着小伙子留下的脚印,迎着风雪蹒跚行走。路灯灯光昏暗,映的白雪闪闪发光。雪落在鼻尖,转瞬化为冰水,落在心头,却结了层厚厚的冰......
此时,小李哥和他的妻子正依偎在一起立在窗子前,看着窗外绚丽绽放的万朵烟花,璀璨了整个天空,照亮了游子回家路。他们的嘴角始终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比蜂蜜还甜!
李老汉破例在这深更半夜扯开嗓子又唱了一回汉山樵歌:“天蓝蓝花艳艳,家在那道坎坎,老汉来把歌谣唱,肩上的柴啊是一担担......” 歌声高亢婉转,穿云石裂,有股“力拔山兮”之意,但它却像一把冷冰冰的冰锥子刺入人的心脏。谁也不会晓得,那是他撕心裂肺的控诉。
这就是我的家乡——汉中。它虽然不是繁华之地,也不是富饶之乡,但它却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正是这只“大公鸡”身上的“一根羽毛”,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有情的汉中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是啊,我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黄土地爱得深沉,我在此扎了根,有了魂,有了汉中情,更有了中国人亘古不变的绵绵情结!
460 |
0 |
2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