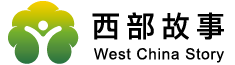生我者,父母也;养我者,婆婆。
家里的几亩薄田不能担负起一家老小生活的重担。爸爸妈妈随着年轻人离乡打工的浪潮,到异乡讨生活去了,留下刚满月的我和年迈的爷爷婆婆。从我有记忆开始,爸爸妈妈只是在春节时才出现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容颜。
我是在婆婆的背上长大的。农村里的活计很多。婆婆既要做繁重的农活,又要照顾年幼的我,根本无暇分身,只能把我用一根长长的布绳绑在她的背上干活。婆婆的背温暖而舒适,在一摇一晃的节奏中,我进入甜甜的梦乡。婆婆的背就是我最温馨舒适的摇篮。每天早上,天刚麻麻亮就为我做好了香喷喷的柴火饭的是婆婆;将我沾满泥土和各种乱七八糟污渍的皱巴巴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让我穿的整整齐齐的是婆婆;泥泞的山路上风里来雨里去送我上学的还是婆婆。
我的婆婆,虽然含辛茹苦养我长大,我却不能用很美好的词语来形容她,因为她的“凶悍”全村闻名。
对我凶悍,自然是“恨铁不成钢”。小时候的我是标准的捣蛋鬼,出名的“小土匪”。婆婆在身后提着一根棒追得气喘吁吁,“小狗日的,老子今天逮到你就求了!”尽管我把全身的力气都用来跑了,无奈人小腿短,总是被抓住,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撕心裂肺又带有夸张表演的嗥叫经常响彻小山村。幼小的我对婆婆的印象就停留在那根不粗的细棒,不重的拍打上。
我不爱读书,仿佛和书本有不共戴天之仇。可婆婆却对我期望颇高。她常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喂头猪!”而我常常走到半路就就以肚子疼为借口,转身跑回家去。不敢让婆婆看到我,蹑手蹑脚地把书包放到家里,像小偷一样不敢弄出半点声响。可是在房外田里劳动的婆婆总是会发现我,悄悄在我身后,一手拿着一根细棍,幽幽地问:“今天是放学放得早,还是你又没去学校?”更多的时候换来的是随着我的一声尖叫,手起棍落,像赶牛一样把我打去学校。我猜田埂上的每一棵草都沾过我的泪水。我在家只要作业还没做完,她是不会让我做半点家务活的。即使是在农忙时节,她常常和爷爷忙到晚上十点,但只要我手上还拿着笔,她绝不会打扰我。我也很争气,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婆婆就会带着自豪的神情向亲戚们炫耀,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有一段时间,二爸出去打工,把年幼的弟弟留在家里由婆婆照看。弟弟很霸道,他占着我吃饭的小碗,睡我的小床。“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婆婆总会说:“你是哥哥,让着他点。”可只要我做作业或看书的时候弟弟来打扰我。我婆婆就会一只手抓着弟弟的一只胳膊,一手拿着扫把往弟弟的屁股上招呼,吓得弟弟再也不敢来打扰我。
那一年,苍老的村小送走了我们最后一批孩子;那一年我去了镇上的完小;那一年,外出打工的妈妈回家照顾我;那一年,2008。
妈妈回来了,她说要照顾我到上高中,婆婆极不情愿的把我交了出来,我看到婆婆的眼底闪过一丝灰色的光芒,仿佛黯淡了许多。多年来的独立操持所有家务,让婆婆变成了一个一个极其好强的人,而我妈也不肯低头,她们常常会为了一点小事吵的不可开交。从我住校时,几乎每周回家都看到婆婆和妈在吵架,可是妈妈吵架哪是婆婆的对手?所以,每次交战都以妈妈一声不吭走进屋看电视,婆婆一边喋喋不休的碎碎念一边不时地瞥屋里结束。一会过后,她的念叨一直没有回应,她便不出声了,继续去田里干活去了。爷爷有时也会在中间劝架,可总是会换来婆婆一顿骂,婆婆骂爷爷时总是咬牙切齿、掏心掏肺地骂,可能是因为爷爷有旧伤,不能干重活,婆婆总是骂爷爷窝囊废,而爷爷自知无法反驳,唯有阴着脸不说话。
长期饱受贫穷折磨的婆婆不能容忍自己吃一点亏。她的东西别人是绝对碰不得的。即使借了她的东西还的时候有一点点损坏,她也会像炸毛的母鸡一样,一顿大吵,空气都会变的压抑。她吵架的本领不是谁都能比的,骂人时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别人,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有时还会咬着牙齿、双脚不安分的在地上踱步,有时又像要跳起来一样。有一回她的一只鸡不见了,而二婆又碰巧倒了一堆鸡骨头,婆婆扯着喇叭似的大嗓门对着二婆家骂了整整一个晚上,骂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像利剑一样戳人心窝,把人戳的血淋淋地,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二婆家的狗对着婆婆叫了半晌,大概也觉得无趣了,索性趴在地上打瞌睡。寂静的夜里只有婆婆中气十足的嗓音在空中回荡。
身体原本就差的爷爷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子女都远在异乡打工,没有返回照顾的意思,照顾爷爷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婆婆的肩膀上。初到城市的婆婆显得很无措,没有了平日里的那股锐气,常常抱怨找不到厕所门,不知道在哪缴费取药。可婆婆从来没有埋怨爷爷一句,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每天早早起来,先把爷爷的全身擦得干干净净,枕头垫的舒舒服服的,伺候好爷爷上完厕所,再去给爷爷端回暖暖的饭菜。而背着爷爷,我却常常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我知道,一方面是因为爷爷的病,另一方面是沉重的医疗费用。
回到家后,婆婆一边干活一边照顾生病的爷爷。在有阳光的午后,她扶着爷爷到院子里晒太阳,她一边摸着爷爷的手一边说:“老头子,快点好起来啊.”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柔柔的,我却感到鼻子发酸。都说养儿防老,可是,当病痛来临时,儿在哪呢?最终,爷爷没能好起来。
“文革”时跟几个男人打架,她没哭;被祖母打骂时,她没哭;背柴时摔到沟里,她没哭。爷爷出殡的那个早上,婆婆却哭完了一辈子所有的泪水。她哭了,她哭她贫穷的一辈子,她哭她所有的委屈。哭她以后她一个人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我听到有人说:“做戏给谁看?哪个不知道她对老头子怎么样?”可是半夜她摸着爷爷的照片叹息时没人看见,她望着那座孤零零的土堆发呆时没人看见。
后来,婆婆生了一场大病,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消瘦了许多,神情变得呆滞,习惯了自言自语。
现在,婆婆老了,笔挺的身板佝偻了,皱巴巴的脸上泛着蜡黄。独自一个人守着老屋,陪伴她的只有忠厚的老黄狗。不知道在哪一天,我的婆婆也会和爷爷一样,只能出现在我的梦里。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不知有多少人像婆婆一样,操劳一生,本图老了能安享天伦。然而,当他们真的到了风烛残年,却成了子女的累赘,仍旧逃离不了孤独的晚年。当期盼、等待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一抔黄土便成了永远的归宿。
781 |
0 |
1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