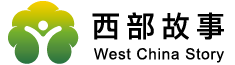初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我和父亲踏上了回天水的归乡路。我的父亲已有三年没有回家乡了,一路上他显得特兴奋,伴随着车厢里悠扬的思乡曲和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村庄与山坳,我们也尽最大想象地谈论着家乡的发展与变化。

下了火车,又经过汽车一路的颠簸,我们终于回到了久别故乡—舒家坝!立刻映入眼帘的是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世界。三月的秦岭山脉,万物还沉睡在厚厚的雪被之下,空气中透出彻骨的寒冷。

爷爷早就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看着爷爷慈祥而沧桑的脸庞,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泪情不自禁的填满眼眶。家里熟悉的那老屋,老树,老井都没变,唯有变化的就是爷爷更加年迈而苍老了。

吃过午饭,我悠闲地漫步在小巷中。突然,一座崭新的大楼房矗立在我的面前,一打听,才知道这是爱心人士资助地方兴办的一所学校。看到家乡这么重视教育,我心里格外欣慰。

在老家的这几天里,虽然时间很短,所见所闻,对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启迪,故乡——我的根,永远是我汲取营养,健康成长的地方。

初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我和父亲踏上了回天水的归乡路。我的父亲已有三年没有回家乡了,一路上他显得特兴奋,伴随着车厢里悠扬的思乡曲和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村庄与山坳,我们也尽最大想象地谈论着家乡的发展与变化。

下了火车,又经过汽车一路的颠簸,我们终于回到了久别故乡—舒家坝!立刻映入眼帘的是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世界。三月的秦岭山脉,万物还沉睡在厚厚的雪被之下,空气中透出彻骨的寒冷。

爷爷早就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看着爷爷慈祥而沧桑的脸庞,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泪情不自禁的填满眼眶。家里熟悉的那老屋,老树,老井都没变,唯有变化的就是爷爷更加年迈而苍老了。

吃过午饭,我悠闲地漫步在小巷中。突然,一座崭新的大楼房矗立在我的面前,一打听,才知道这是爱心人士资助地方兴办的一所学校。看到家乡这么重视教育,我心里格外欣慰。

在老家的这几天里,虽然时间很短,所见所闻,对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启迪,故乡——我的根,永远是我汲取营养,健康成长的地方。